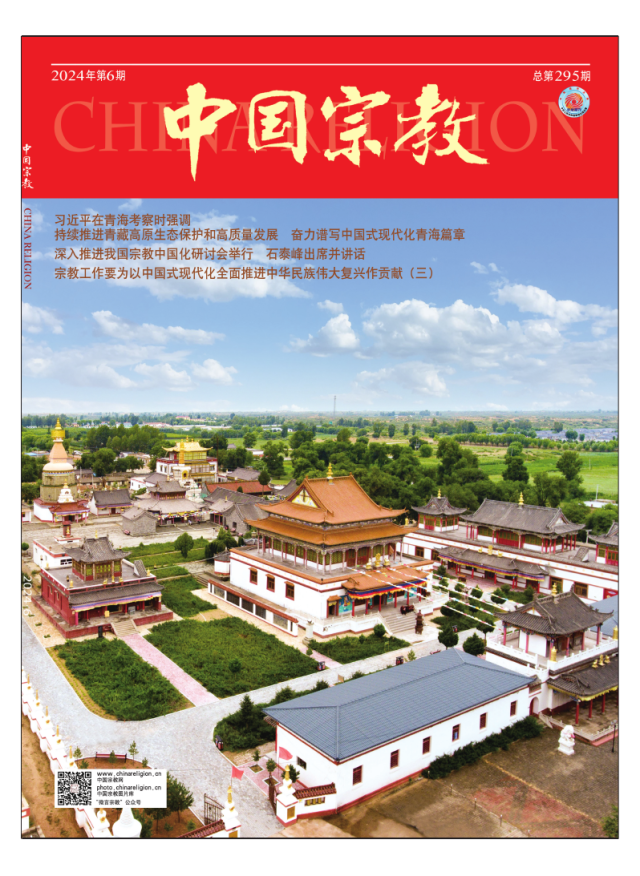
《中国宗教》2024年第6期封面
中国大运河源远流长,大运河文化博大精深。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漕运通道,也是南北文化交流的孔道。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沿着大运河广泛传播,使其成为一条宗教信仰文化传播的廊道。大运河沿线的道教文化,因为承担着重要社会功能而流传演变,也是大运河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
大运河是一项中国古代创造的宏大工程,始凿于春秋时期、南北贯通于隋唐、截弯取直于元代、兴盛繁荣于明清。实际上,大运河是由不同的河道构成,它们分别流经不同的地区,各自因而也拥有不同的历史起源。元朝政治中心北移,“前代呈多枝型分布的运河至此转变为单线型运河,从而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域更加直接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中国运河变迁史上自隋唐以后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规模”。(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不过,元朝国祚不久,运河通航时间短,运河体系始终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于是海运逐步取代了它而成为粮运的主要形式。([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
相比海运,大运河无疑是更加安全的,因此终明一世,这条人工运道一直发挥着黄金水道的作用。清朝为了实现南粮北运,仍然继续启用大运河这条生命线。明清两代均视漕运为国之命脉,故对元朝大运河进行整治改造,在各方面使之更趋完善,持续畅通四五百年之久。大运河的持久性对运河文化区域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隋、唐、宋、元是运河文化的萌生及初步形成时期,那么,明清两朝则是运河文化的兴盛时期。(李泉:《中国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演进》)漕运的发达、商业的繁荣、人口的流动、文化的交流等等,促使该区域社会逐渐融汇积淀了丰厚的精神文化。
大运河文化即因大运河而生、而变、而传播的文化,具有开放、包容、融合、交流等多方面特征。(王加华、李燕:《眼光向下:大运河文化研究的一个视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也沿着大运河广泛传播,使其成为一条宗教信仰文化传播的廊道。
二
道教起源于齐、燕一带的巫术和神仙之学,至东汉末年原始道教分为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个支派。张角创建的太平道曾在青、徐、冀、幽、荆、扬、豫、兖八州发展信徒,几乎涉及除关中之外的运河区域所有州郡。汉献帝年间,由张道陵创建的五斗米道取得合法地位,故得以在运河区域流传。到了晋朝道教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宗教体系,也自然吸引了历代统治者的注意力,这在明朝也不例外。只不过明时道教两大派别正一道和全真道,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待遇并不相同,此不赘述。清初对道教基本沿袭明例予以保护,并从维护统治目的出发,认为“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返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04)道教是一种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举凡天神、地祇、仙人、动物等都被纳入供奉的神灵系统,反映了人们对于日月、星辰、山川、河岳、祖先、亡灵等崇奉的信仰习俗文化。
明清时期的大运河流经浙江、江苏、山东和直隶四省,南北各地区域文化得以联结在一起。从道教文化来看,明朝以前位于大运河北部的齐鲁和京津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比较单一,除了官方倡导的城隍神、土地神之外,较为普遍的只有碧霞元君和东岳大帝了。其中,碧霞元君是北方地区最为重要的女神,而在道教尊崇的女性神灵中,也常有“南有妈祖天妃,北有碧霞元君”之说,足以见其在区域社会里的影响力。位于大运河南部的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人们的宗教信仰则复杂得多,表现出明显的泛神崇拜特征。大运河南北贯通以后,对水道运输的依赖以及商贸往来的繁荣,致使在北方运河沿线的乡村、城镇中,自然神、行业神、圣贤神等崇拜日益增多。运河南端的一些神灵也传播到北方,同样受到更多人的祭拜。这些神祇在大运河流域传播开来,并渐渐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成为客居人口和土著居民共同信仰的对象,体现了道教信仰的实用性、多元性。(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
例如,在水神信仰中,金龙四大王在山东济宁一带兴起后,便沿着大运河向南北传播,以“捍御河患、通济漕运”为诉求,不仅“北方河道多祀真武及金龙四大王”([明]谢肇淛:《五杂俎》卷15《事部三》),而且“江淮一带至潞河,无不有金龙四大王庙”([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5《金龙四大王》)。其实,在明朝以前尚无专门的漕运水神,明时漕运之险与金龙四大王信仰兴起有着重要关系。(蔡泰彬:《明代漕河四险及其守护神——金龙四大王》)作为海运与河运航行保护神的妈祖(又称“天妃”“天后”),从福建乘水而来遍及大运河沿线,凡“军营漕运之所,江海河汉之滨,悉崇奉之”([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福建商人的北上和官方的倡导,共同导致妈祖信仰在大运河区域的盛行。晏公原本是江西的地方性水神,明清之际作为保障行舟安全的神灵,得到了很多漕运官兵的崇祀。
关公信仰的传播与大运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关公虽不是水神,但随着山陕商人出入大运河,自然也成了保佑航行安全和商业兴隆的神灵。关公即关羽,又称“关帝”“关老爷”,他是一位被神化的《三国志》英雄。在关羽身上有着足以作为神而受到信仰的生存方式,其信仰特点在于从武神转向财神(商业之神)而被人们供奉。大运河与黄河的关系尤为复杂,一部大运河变迁是就是一部黄运关系史。(邹逸麟:《历史上的黄运关系》)在明朝,关公曾作为帮助治河的水神而受到信奉。万历年间,积极治理黄河的总理河道御史潘季驯奏请应赐予关羽封号,原因是其在治河过程中显灵。“官、民、商以关羽信仰为纽带结成一体,共同完成了治理黄河的工作。由此,我们便可以窥见关羽信仰与晋商一同扩及运河地区(包括漕运路线)的原因。”([日]渡边义浩:《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
三
道教文化在大运河沿线的传播,留下了许多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明清时期,在大运河沿线的城市中分布着大量道教宫观。作为大运河重要的“繁华商埠”临清建有较大规模的道观约30多座(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寺观志》),构成了人们的信仰空间,成为当时城市生活的重要部分。“枢纽要地”济宁的宗教文化景观也颇为引人注目,大运河所推动的城市化、商业化塑造了开放、高端、包容的社会风气和城市环境,促进了当地精神文化和正规宗教的繁荣。(孙竞昊、汤声涛:《明清至民国时期济宁宗教文化探析》)至1950年前后,历经战乱动荡的济宁依然有多所著名的道观屹立于城内外。(赵玉正:《昔日济宁城区著名道教庙宇宫观》)
根据历代地方志和庙宇碑刻资料相关记载,以大运河穿行及邻近府州为统计单位,我们能够大致统计出明清时期大运河区域庙宇建筑的分布情况。明清时期各类文献有明确记载的大运河沿线金龙四大王庙计有100多座,大运河沿岸各州县几乎都有该庙宇的分布,而且从地域分布上来看,黄运交汇、治河频繁的苏北地区该庙宇数量最多。(褚福楼:《明清时期金龙四大王信仰地理研究》)祭祀妈祖的庙宇有多种称谓,如“天妃宫”“天后宫”“显惠庙”“惠济祠”等,这一时期大运河沿线的妈祖宫庙计有60多处,其信仰在时间和地域上呈现自南向北的传播趋势。(胡梦飞:《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天妃信仰》)与此相较,晏公庙宇计有20多处,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多,但地域分布比较广泛,南自杭州,北至通州,大运河沿线各州县几乎都有它的踪迹。(胡梦飞:《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晏公信仰》)在运输发达的水陆通衢,山陕商人集聚的会馆便是关公信仰集中分布的地方,他们在大运河区域创建的会馆通常都采用关帝庙的形式。明清时期,大运河山东段的城镇是山陕商人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又以聊城、临清最多。清朝咸丰年间,在聊城经商的山陕店铺已达近千家,有“西商十居七八”之说。(张士闪:《中国运河志·社会文化》)粗略统计,明清时期大运河山东段关帝庙数量多达三四百座,由此可见关帝之信仰盛行。
大运河沿线庙宇的广泛建立,以神灵为依托的庙会、酬神活动也随之兴起。如天津天后宫建立后,祭祀妈祖的庙会规模宏大,集迎神赛会和商品贸易于一体。天津的庙会最初被称为“娘娘会”或“天后圣会”,由于在清朝受到康熙帝、乾隆帝的恩赐,后来就称为“皇会”。“三月二十三日,俗称为天后诞辰”,“神诞之前,每日赛会,光怪陆离,百戏云集,谓之皇会。香船之赴庙烧香者,不远数百里而来。由御河起,沿至北河海河,帆樯林立”。(望云居士:《天津皇会考纪》)“津门好,皇会暮春天。十里笙歌喧报赛,千家罗绮平鲜妍,河泊进香船。”([清]樊彬:《津门小令》)历史上临清庙会众多,规模较大者当属对碧霞元君的祭祀,时至今日每年都要举办盛大的“迎神接驾”活动,成为这座运河城市特有的文化象征。当地有许多民谚反映庙会之盛况,如“临清搭庙会,泰山关庙门”“二州十八县,临清会上见”“不去天津卫,也赶临清会”等。(周嘉:《漕挽纷华:明清以来临清城市空间研究》)江南地区金龙四大王的迎神赛会场景也颇为壮观:“五色牙旗按五方,东西北庙爇真香。更穿白马司徒港,去谒金龙四大王。”([清]洪亮吉:《洪亮吉集·更生斋诗》卷3《续竞渡词十首》)

历史上的临清庙会
总之,大运河是古代先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它以开放性、包容性、统一性的姿态,加强了南北各地道教文化的传播互动。考察道教文化传播的历史,不但对于道教史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为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山东省运河文化研究基地。本文获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专项“京杭大运河商业文化与区域社会研究”(批准号:23CLCJ03)项目资助。]
来源:《中国宗教》2024年第6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